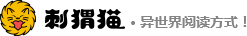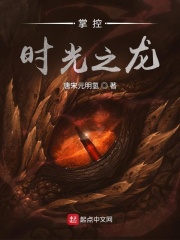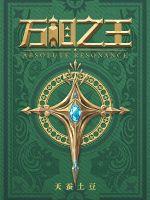几个人驱车来到县城钱庄门前,富贵儿在门外喊了一声,立刻有伙计跑出来迎接,见富贵儿拉了一车的银钱,赶紧打开后门让富贵儿的驴车停进了后院。
这凤栖县是个不大的小县城,平日里哪有这么多银钱的存取,见富贵儿拉了一车的银钱来存,早有伙计去通知了掌柜的。
“呦,是朱家四少爷啊,有请上座,朱少爷要存取直接命下人来知会一声就好,我们会上门办理的,那里还需四少爷亲跑一趟,四少爷请喝茶……”
“茶我就不喝了,我这还有别的事需要处理,这存钱之事,您跟我的账房结算吧,春喜儿这里的事儿就交给你了,钱不要都存,留点钱一会儿去街上买点东西,工坊帮过咱的乡邻都要有点表示……”
说完话,富贵儿迈步走出了钱庄,弄的这掌柜跟一帮伙计目瞪口呆,“好家伙,这朱家四少爷大气啊,这么多的银子交给一个小丫头儿处理,这也太儿戏了。”
富贵儿出了门,刚准备找个茶馆打听点消息,在街上转悠了一会儿,便遇上了也同样来打探消息的三哥。
“四弟,这么早啊,你也是来打探消息的吧?我刚从城里的好友那里出来,说这县城的春兴酒楼有点问题。”
春兴酒楼是栖凤县县城最大的酒楼,酒楼一楼为餐饮,二楼雅间包房,三楼提供住宿,这春兴酒楼装修奢华,能住的起春兴酒楼的人基本上非富即贵,但最近几天整个春兴酒楼的三楼却被一伙外地人给包了下来。
听了三哥打探来的消息,富贵隐隐的觉得这包酒楼的外地人有问题,跟三哥借着去酒楼结算代售门票银子的名义去探了一番,却没探出什么有用的线索,那伙人防范意识很强,去往三楼的楼梯两侧一左一右站着两个门神,看那肌肉骨骼就能看出两个人都是习武多年的练家子。
其实这酒楼确实有问题,此刻三楼的一房间里,那刺杀陈三的刺客正跪在地上认错。
“奴婢做事不利,坏了小姐的大计还望小姐责罚,”黑衣刺客跪在地上,头都不敢抬起来。
“肖总管不是说,这凤栖县没你对手吗?怎么就阴沟里翻了船呢,难不成是你低估了那杜捕头的能力?”女子躲在珠帘之后,背对着跪地的刺客,看不清容颜但衣着华贵,言语里自带让人不敢有丝毫违逆的威严。
“回聘七公……回聘小姐,擒奴婢者并非那杜姓捕头,而是另有其人……都怪小人一时大意才被那人所擒,”对于富贵的冒然出击,一出手便让自己无还手之力,黑衣刺客一直心有不服。
“呵呵,你说的是擒不是伤,看来这人的功夫超你很多,肖总管你可看清那人的面目,这凤栖县不会真的卧虎藏龙吧?”
“回小姐的话,奴婢并未看清,只是感觉那人是个没练过功夫的俗人,出了牢狱跟那天外面值守的兄弟们确认过,小人被擒那日,确实从狱中走出一个俗人,那人不是别人正是那朱家四子……”
“哦,怎么会是他,你们先前查探不是说这人从小痴傻,认字不多也并未习武吗?一个未曾习武的人又怎能擒了你肖总管呢,肖春新看来你不是马失前蹄,你是办事不利啊,回去吧,我这里不需要你了……”
“小姐英明,那朱家四子确实未曾习武,那日奴婢被擒也不是对方使用武技,而是纯纯的蛮力加了一份蹊跷,还望小姐详查。”听了女子的话,黑衣刺客心知自己前途无望,脑门触地言语里更多的是乞求。
“这事我当然要详查,但我这里确实没有你的位置了,你还是回去待命吧……”说完话女子转身离去,不再给肖刺客任何解释的机会。
话回两边,富贵跟三哥朱诚在春兴酒楼没有探到线索,两个人再去劳烦那徐捕头,却也并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,按徐捕头的意思,此事被上面的人给压了下来,那日所有参加抓捕的衙役狱卒全被放了假,衙门内现在到底什么情况谁也不清楚。
从徐捕头那里出来,富贵猛然觉得这背后的黑手过于强大,本来已经板上钉钉马上水落石出的案子,仿佛又进了死胡同。
“三哥,此事就此罢手你甘心不?不甘心你跟我走,”富贵跟在三哥后面,见三哥转身摇头,紧赶两步走到了朱诚前面。
这彩票的印刷跟印章篆刻,富贵都是亲力亲为,带着三哥匆匆去了张记印刷,却见往日里生意兴隆的张记早已人去楼空,找邻居打听了一下才知道,两日前这一家人便搬走了,说是去郡府城投亲去了。
再寻到那刻章胡大的家,也同样如此,这一家似乎走的更早,前脚胡大刚刚入狱,后脚一家人便匆匆搬离了凤栖县。
“厉害啊,办事留有后手,不简单不简单,我还不信了,三哥你可认得去小寨子东村的路,”连吃两盏闭门羹,朱富贵仍不肯死心,带着最后的希望,两个一路打听去了陈三所在的村落。
村里的人听说两人是来打听陈三的,都如同躲瘟疫一般躲着两人,两个人在村子里转悠半天,竟没有探得一点有用的线索,最后还是富贵用糖诱开了街上孩童的嘴。
原来那陈三是村里的泼皮,平时干的都是偷鸡摸狗,夜敲寡妇门日掘绝户坟的事儿,平日里大家不愿招惹他并不是因为他有多厉害,而是这人是个没爹没娘没妻儿的三无人员,你揍他狠了他或是去你地里祸害庄稼,或是去点你草垛,你不愿搭理他他又觉得你好欺负,蹬鼻子上脸赶着吃饭的点去人家里连吃带拿还甩脸子。
所以村里人听说陈三在朱家芦苇地讹钱被抓,后来还被射了一箭生死不知,村里提前就过了年,开祠堂祭祖上香,村里的鞭炮声整整响了一晚上,人坏到这个份上真的也是坏出了水平,前世海龙村里曾有个往水井里拉屎的小子,在海龙心里那已经是算是最恶心人的坏人了,但跟这陈三一比却是小巫见大巫了。
出了小寨子东村,案件所有的线索也就断了,坐在返程的马车上,富贵闭着眼睛苦苦的思索,“背后的黑手用这样一个泼皮无赖办事,这显然早已经做好了卸磨杀驴的准备,那陈三讹钱的事不管成与不成都是一个弃子,现在唯一还能继续查的只能是那个刺客,这刺客所施招式所用暗器本应是突破口,但要从此处下手却如大海捞针,对,记得两人近身肉搏时,闻见两股味道,一股是一种香味,那味道显然比普通家里的香烛要高级的多,还有一股浓烈的尿骚刺鼻的气味……”
什么人会接触香火呢?是庙宇道观里的和尚道士吗,但那香味似乎比起庙宇里的香味又有所不同,那尿骚呢?
“去他娘的,管他呢,咱不惹事也不怕事,事儿来了咱接着就是了,”富贵前世曾是特种部队里的侦察兵,但却不是警察,这断案的事情自己实在是不在行,既然这事儿占不到主动,那就被动承受吧。
这朱家的全家上下似乎都跟富贵的思路一样,虽然大家日子又回到了之前的日复一日,但暗地里谁都能觉察到,大家正在等待着一场暴风雨的来临。
连那平日里没心没肺的邵莹,最近几日都变的格外乖巧,收起平时那大大咧咧的步伐,轻盈的迈着碎步,总躲着富贵跟春喜儿私下里嘀嘀咕咕,要是不小心跟富贵打了照面,也会脸红羞涩的躲开。
“我去,这是要变个活法啊,要走大家闺秀的路子了吗,”看躲在角落里,弓着身子不敢抬头看自己的邵莹,富贵心中暗暗的思索,嘴角却禁不住扬起了戏谑的坏笑。
有了那一夜的知心交流,邵莹真的不再三人挤一张床了,起先春喜儿也陪着她一起搬去了隔壁的屋子里睡,但四天后春喜儿却又抱着枕头回来了。
“怎么又回来了,邵莹那丫头去隔壁睡,是给你腾地方连屁股的吧?”见春喜儿熄灯上床,富贵嘴里说着戏谑的话,一把把春喜儿搂进了怀里。
富贵这几天搞赛马又四处奔波着案子的事,身体又壮实了不少,自我感觉小兄弟的个头又有些增长,比前世自己十五六的岁时候也差不了多少,这几天正有跃跃欲试的冲动。
“少爷,少爷,不是了……那邵莹成人了,来了葵水……”听了富贵的话,春喜儿羞的满脸通红,却躲在富贵怀里道出了秘密。
“啊,真的啊,怎么就无缘无故的就来了呢,哈哈,我知道了,肯定是那晚你摸人家来着,快跟我说说,你是怎么摸的,是这样吗?哈哈哈……”
“少爷,你坏死了,你全听见了吗?哎呀羞死了羞死了,不理你了,”听了富贵的话,想想那晚跟邵莹在床上的胡闹,春喜儿已经羞愧到了极点,用薄被盖住自己的脑袋,再也没脸见富贵了。
轻轻的搂着春喜儿娇小的身躯,感受着她躯体因羞涩而带来的温度,夜很静,只有那鸣虫吱吱的叫声,心也很静,那股莫名的冲动被一份安逸的温暖所替代。
“少爷,你是不是……是不是很想……要不你来吧,我不怕疼,”小丫头躲在被子下,见富贵久久没有说话,小心的撩开被子,身子紧紧的贴着富贵壮硕的身躯,言语轻柔而又甜蜜。
“春喜儿,这树上的果子熟透了才好吃,没有熟透的时候虽然有点甜味但它是青涩的,你是少爷我精心培育的一颗果子,迟早都是我的,我要等着熟透了再吃,”富贵说着话,轻轻撩起春喜儿的肚兜,头埋了下去。
“少爷,少爷你不是……不吃的吗?那,那是给孩子……”
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,一夜的细雨绵绵,滋润了这片干涸的土地,也滋润着少男少女们羞涩而又炙热的心。
朱家大院等待的那场暴风雨终究是没有来,连绵的秋雨连下了三天,三天后雨过天晴,那县衙里青天大老爷也乘了他那座小娇晃晃悠悠的进了朱家。
“老四,老四,那县衙里的县太爷来咱家了,爹爹喊你过去说话,”这一日富贵正在院子练他的军体拳,三哥朱诚气喘吁吁的跑了进来。
“县太爷来干嘛,不会是案子有新进展吧?”富贵儿拿起春喜儿递过来的毛巾擦了擦汗,急切的问道。
“我也不知,只是爹爹传了话,让你速去。”
“走啊,这还等啥,”富贵把手里的毛巾扔给春喜,跟着三哥就走。
“少爷,少爷你倒是换身衣裳啊,”看着富贵匆匆而去的身影,小丫鬟急得直跺脚。
这朱家大院比三哥富贵儿心急的大有人在,等两个人匆匆赶到老爹院子的时候,院子里早已经站满了人,两位姨娘二哥大哥大嫂正对着屋前站着,唯独不见那传说中的四姨娘,一群丫鬟仆人分散在四周,大家都没有什么言语,但表情里多透露着紧张与焦虑。
朱家出了人命案子,这对这个小县城来说都算是大事,况且最近大家都知道了,这背后有高人要对朱家动手,今后大家是否还能过这太平的日子,这几天一直成了大家心中的魔咒,此咒不解身心难安,连睡觉都睡不踏实。
“让老四朱晟进来说话,”大家焦急的等待中,屋里终于传出了话。
富贵左右环顾看向自己的目光,整了整被追来的春喜儿给换下来的新衣,这才迈着沉稳的步伐迈进了屋子。
“小民朱晟见过大老爷,给大老爷请安了,”这富贵没跟管家人接触过,也不懂这些规矩,记得电视里都是这么演的,说着话便欲跪下磕头。
“哎呀,快快起来,这里又不是县衙大堂,我今日来此只算是私人拜会,不用行此大礼,”这县太爷见富贵要下跪,紧忙起身把富贵给搀扶起来。
“儿啊,这大老爷是爹爹的旧交,今日前来是有事与我商量,这事爹爹还要听听你的意见,所以把你喊进来,一起商讨……”
“嗯,这个案子上面接手了,朱家也没有什么损失,此事后朱家安心过活就是了,只是这郡府下了令,说看上了朱家的芦苇地,欲征地牧马,所以本县今日登门就是与朱家公商量此事……”
“征地牧马,有偿还是无偿?”富贵待县太爷说完话,嘴里轻声嘟噜出一句,心里却在暗暗的嘀咕“我靠,转了这么大一个弯儿,敢情是看上我的芦苇地啊,破地没人耕,耕了有人争,这都什么事儿?”
“哈哈,四公子放心,肯定是有偿,如若强征贴个告示知会一声便是了,哪里用得我亲自上门商量,我刚才已与令尊谈了十之八九,只是令尊称此地分家已经归于你名下,这才喊你进来相商,”富贵的话有些生硬,所以县太爷的口气也有些不善。
“哦,这样啊,现如今我虽已分家,这事儿还是全凭爹爹做主,”富贵心知这土地买卖租赁之事自己根本不懂,老爹把自己叫进来多是怕以后落了什么把柄在衙门手里,所以还是把决策权交给了老爹。
“此地地契已在我儿手里,一共三十亩,此地以租赁的形式租给官家,合同起签五年,每年租金三百纹银,租金年付,我儿对此可有异议?”老爹说着话抬头看向富贵。
“好,很好……”“爹爹满意就好,儿并无异议,”富贵本想发表肯定的意见,但心想你们都商量好了,这里哪有我说话的份,所以后面还是改了口。
“好,那这事就这么定了,”县太爷似乎很想快速解决此事,此时见大家都没意见,赶紧让随同的师爷起草合同。
签字画押按手印,一番繁琐的交易流程走完,县太爷乐呵呵的拿着合同回去交差去了,显然这背后之人的官位要比这县太爷高很多。
看着桌子上的银子,富贵心里有一股莫名的失落,就这么没了,虽然这银子给的远远超出买地的费用,但芦苇地是自己梦开始的地方是自己用心的投入。
“儿呀,这事你心里到底是啥想法?”老爹送走了县太爷,见儿子痴痴的傻站那里发呆,禁不住问道。
“还能有啥想法,自古民不与官斗,别说给钱就是不给钱,咱还能反抗不成,罢了,每年有这三百两,也是物有所值……”
“哎,我儿能这么想实属不易,拿着这些银子速速回你的长工房吧,这院子不是你该待的地方。”
老爹下了逐客令,富贵儿收起桌子上的银子,匆匆出了屋子,带着春喜儿朝芦苇地赶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