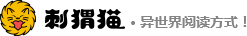孟玲玉看到外面两个垂头丧气的孩子,心里不是滋味,她挂断了那个没有任何用处的慰问电话。
这下子她的期盼再也没有了,就只剩下她的宁宁。她擦干了眼泪,来到梳妆镜前画了个让她气色变得好的淡妆,然后再将头发盘起来,换上了黑色的衣服走出房间。
她原本以为一生真的很短,现在感觉很漫长,她看向自己的手表,怀疑它是不是坏了,为什么会过得那么慢。化好的妆又被泪水浇花了,她从没想过生离死别经历起来,会那么的痛,刚刚强装镇定,现在回忆起来不堪一击。
张宁醒过来,眼睛怔怔地看着洁白无瑕的天花板流泪,明明找到了他,为什么要给她这样的结果,她不明白。
女人不管怎么哄她,她的眼泪一直在流,眼睛也不动了一下,只是看着天花板流泪。她坐在旁边默默替她眼泪,问她为什么流泪也不回答。
心理医生来到病床前给她打了安眠剂,她才闭上眼睛。
“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告诉她这个消息,她还是个孩子她能承受得了吗?”站在天台的花常富愤怒抹了抹脸上的雨水,走来走去看向面无表情的夏树说到。
“那是她的父亲,如果不告诉她,又会多少人记得他?除了我们几个还有上面的几个,试问还有谁?”夏树眼神平静地看向他,说到。
花常富愣住了,“是啊,要是我也像他们一样,谁会记得我?我一个亲人也没有了。”想着想着他眼角泛起泪花,任凭雨水打湿他的脸,他也不擦了。
深夜穿着病号服的张宁,站上天台的边沿,看着下面雨水斑驳折射的灯光,觉得耀眼极了。
她的手背有一块地方露出骨头,血水不断从里面流到她手心里,再从手心里流到地上沿着雨水淡去,直至无影无踪。
打完热水回来的护工被吓了一跳,白色的地板上有一滩血,水果刀沾满了鲜血。脸色煞白,冲了出去叫人。
沿着血迹夏树走到天台上,就看到张宁一个人站在天台边沿的上方,他看到这一幕,心跳慢了半拍。他慢慢走过去,轻轻喊了她一声。
她没应,她拿着小口琴正在吹《夜莺》,《梦中的婚礼》。天色太暗了,看不清楚她的表情有多难过。
吹完一曲后,她转头看了一眼身后的人,“我没事,我在送一个人回家,不要打扰我好吗?真的不要打扰我,吹完我就回去,不然我真的跳。他太久没回家了,让春风伴着音乐带他回家吧。”
说完了,她又吹起《梦中的婚礼》,小时候,她一直记得这是他和妈妈常常四手联弹的曲目。哎,老爸看你没有机会了,以后就由我来吧。
只是有个条件,下辈子我要做你和妈妈的亲生女儿,像哥哥姐姐一样一母同胞。
《梦中的婚礼》让她吹得更加悲伤了,夏树接过伞,帮她撑着伞。
夜风轻轻,细雨绵绵,世界还是那个世界,时间还是那个时间,只是在某一瞬间已经是物是人非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