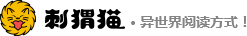花常富和段长庚对视一眼,花常富先裂开嘴笑问他,“中午好,段总。”
“中午好,花总。”段长庚点点头回应,电梯门开后,伸出手去又说,“你先请。”
“段总最近你们熬的汤,我可以分到喝汤吗?不吃肉。”花常富和他一起地下车库走去,一边走一边点起香烟问道。
段长庚走到自己的车前,打开了车门转过头正在抽烟的花常富说。“难道你不怕吗?太多说破了,就像破了鸡蛋一样,会变臭,变得一无用处。”
“开弓没有回头箭,就算臭了也知道它是不是糖心蛋。你说是吗?”花常富望着眼前这个脸上有道深深刀疤的人,说着别有深意的话。
段长庚冲他颔首,说了一句,“回见。”坐上了车,关了车门不一会才开走。
花常富靠在自己车上,一脸惆怅的抽着那只剩半截的烟。
花简看到摘下眼镜的张宁,坐在木椅上望着水平如镜的湖面,手里握着口琴,在吹着断断续续不知名的曲儿。带着热浪的夏风,袭上她冷漠的脸。她的短发在后面飘扬,眉毛深深地皱在一起。
何为信仰?何为叛徒?一前一后中间过渡了什么,才落得叛徒罪名?她心中每问一句,她就用口琴来用信任过滤回答。
信任像一块很厚很厚的滤镜,它可以抵挡无数次外面不良好的因素,但也易碎。碎了支撑起来再也不经一次动摇了。
原本目光追逐远处余安的花简听到了这断断续续的琴声,不免徇音看了过去,看到独自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的张宁。看到远处的余安,不再跟在她后面了,她不免得有些窃喜。
“记得你曾是条子,还是个叛徒。进去也不得不到。”王池在他耳边小声地说,就推开会议室的门走了进去。
花常富看向他低下头挝耳揉腮,强忍住把他剐的冲动,露出可掬的笑容走了进去。他们看到坐在中间位置的不是周浦,而是段长庚。两个人也疑惑了起来,怎么他一个人来了,还坐在中间。
……
坐在窗口旁穿着淡青色对襟衣裙的老人,夕阳照在她枯瘦的身上才显得她熠熠生辉。一本厚厚黑皮本放在她的膝盖上,旁边小圆桌上有一个小茶杯和放着纯音乐的小收音机。
“您好,老师。”张宁在保姆的带领下,走到她面前低下身去,和她平视。
“啊,小宁啊,你好久没来看我了。”差不多90多岁的老太太说着慢慢睁开眼睛,满是皱褶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。
“抱歉,我应该多来几次。”握住她伸过来的刻满皱褶苍老的手,低下头面露惭愧说到。
老太太仔细看了她一下又下,摸着她那张瘦削的脸。“来坐下,你生病了吗?怎么瘦了。”
张宁摇摇头笑了笑说到,“没有,瘦了挺好的。”坐到旁边椅子上。
“没有就好,今天为什么没有去武术馆啊?来这里。”老太太看向她问。
“想您了,来看看您。”
“我老了,记忆开始混乱模糊了,清醒的时间也越来越少。我不记得你了,你就不要来了。不要伤心难过,这个世间是个圆,不管多少离别都割不开想要的重逢。我把它交给你了,希望你未来能在自己喜欢领域科研的路上越走越远。你奶奶学生时期就想要它的,一直没能给到她。”老人把膝盖上的本子递给她。
张宁接过后道谢,看向老人又说,“生命为什么一定要死亡?”
老人听后哑然失笑,回答道,“生命的尽头就像圆周率3.14无限不循环小数。永远朝着生生不息走去,怎么会是死亡呢?”